作者:丁玲 诵读:王卉
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,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。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,谁还有幽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?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,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。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。

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,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,那时山西还很冷,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,习惯于粗犷的我,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,紧紧闭着的嘴唇,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,使我觉得很特别,而唤起许多回忆,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。
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,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,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,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。但我们都很亲切,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。我们都尽情的在一块儿唱歌,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。
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,在情感上,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,然而彼此都能理解,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,而揶揄。
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,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,我们也痛饮过,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,我们也互相倾诉。
然而现在想来,我们谈得是多么少啊!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,尤其是我。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,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,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,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。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,因为,像这样的能无妨嫌、无拘束、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!
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,平静的住一时期之后致全力于著作。抗战开始后,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。她或许比较适于幽美平静。延安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,然在抗战中,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,而策划于较远大的。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,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。
但萧红却南去了。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,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,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原故,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,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。

我们分手后,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,端木曾来过几次信,在最后的一封信上(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)告诉我,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。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,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。
有一次我同白朗说:“萧红决不会长寿的。”当我说这话的时候,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,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,能够耐苦的,不依赖于别的力量,有才智、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,是如此其寥寥呵!
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,当我昂头望着天那边,或者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,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,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,多一个真实的同伴,便多一份力量,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,指示光明,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;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拘于个体的偏狭之中,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。我们要使所有的人,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,和为这享受而有的伟大牺牲。
只要我活着,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。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,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,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,何况更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,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。
我要借这风雨,寄语你们,死去的,未死的朋友们,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,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。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,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,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。
风雨已停,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山头上,明天将有一个晴天。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,为着永生而休息。我吹熄了灯,平静的躺到床上。
【如果您有新闻线索,欢迎向我们报料,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。报料微信关注:ihxdsb,报料QQ:3386405712】
注: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,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,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,情况属实,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,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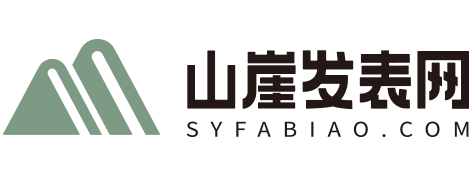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